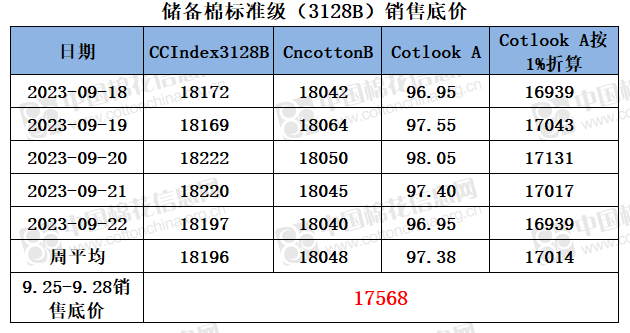
2023年7月,沈从文先生的助手、著名纺织考古专家王亚蓉编著的作品《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在中国纺织考古领域是一本承前启后的作品,体现了作为中国百年考古重要组成部分的纺织考古半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这本书回顾了沈从文、王、王亚蓉等人走过的艰辛考古之路,展现了第一代纺织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发掘、保护、传承中华服饰文化的奋斗历程。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肇始于沈从文
考古是一项探寻文明起源的工作,对于人类探寻本源十分有意义,但这项工作十分艰辛,而其中的分支——纺织考古更甚。纺织考古学界有这么一句话,“千墓难得一衣”,特别是丝织品,作为有机质蛋白类文物,容易腐坏,极难保存。对纺织品的发掘都是最急迫、抢救性的,环境条件特别艰苦,结果又不可预测,因此做纺织考古工作之不容易常人难以想象,但是意义非常重大。
《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一书中谈到,1964年,周总理多次出访欧洲以及东南亚地区,经常被这些国家领导人带领参观服饰博物馆,他认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也可以编写一部服饰图书作为馈赠国礼。时年62岁的沈从文接领了任务,便开始埋头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之后十多年几经波折,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著作终于在1981年出版。沈从文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肇始。
对于服饰研究这个课题,沈从文曾说,他要谈的不是服装,而是一种工作方法。这本书的编著者王亚蓉也说,对文物深有研究的沈从文一直讲究“史实相证”的唯物主义方法。他对各类文献非常熟悉,1950年后更是将精力全部投入到文物的钻研之中,无论是器物、绘画还是原始的骨、针都让他沉迷。因而在服饰实体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沈从文充分利用易保存的文物资料,如陶俑、壁画等,与文献资料进行充分比证,以此作为服饰研究的先期基础。
“我们研究服装不是为了好看才搞,也不是为了演戏搞,我们可以探索许多历史细节,和史料互相印证。”沈从文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在古代服饰的研究中,沈从文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对一些既有的结论提出了质疑,比如,《韩熙载夜宴图》不一定是南唐时期所作,而且可能是拼凑起来的。这是从服饰的角度提出的新的怀疑。
沈从文注意到,虽然唐人和宋人都穿圆领衫子,却没有人注意唐、宋的圆领完全不同。唐朝的衣服是圆领的,没有内衬,而宋朝和元朝的领子里面都有白色衬里。大量壁画可以证实,领子内有衬里是宋朝制度,而《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男性圆领衣服多是如此。画中还有一个人身上悬挂了个“帛鱼”,这是唐朝初年的制度,元和以后的画作中没有发现过。此外,按照宋朝新立的制度,凡是不做事的人都要“叉手示敬”,画中人、甚至包括一名和尚也遵守这个规矩。所以,沈从文认为《韩熙载夜宴图》可能绘制于北宋初期,而不是南唐。
迄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40余年,仍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
王㐨主持发掘马王堆汉墓
半个世纪以来,在沈从文的指引下,王㐨、王亚蓉等纺织考古人忙碌地奔赴各大考古现场,发掘、保护、研究、修复了一件又一件的纺织品,如河北满城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南信阳殷墟妇好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广州南越王墓、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北京大葆台西汉墓、江西赣州慈云寺、河北隆化县鸽子洞、江西海昏侯墓……这些考古发掘现场,完全可以串起一部中国纺织考古史。
王㐨与沈从文相识于1953年,当时他游览故宫,沈从文作为讲解员给他讲解了一个唐宋铜镜的展览。后来王㐨得知沈从文的身份之后,曾问他为什么其人与小说完全脱节。对此,沈从文的回答是“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后来王㐨也走上纺织考古之路,并且经常向沈从文请教一些问题,他曾提及沈从文为玉衣命名的事情。此前考古队员曾经挖出一些零散的长方形玉片,四个角有孔,在博物馆展出的时候被视为古牌式玉片。沈从文判断,这可能就是史书上说的金缕玉衣。1968年,考古队员从河北满城汉墓挖出一件完整的玉衣,证实了沈从文的说法。
后来,王㐨也成为一名考古专家,并于1978年主持发掘了长沙马王堆汉墓,这是国内成功科学发掘并保存为数众多的纺织品文物的里程碑式工作。这项工作的成功为纺织品的发掘和保护打下了基础,让纺织品的“保存”年龄一跃超过两千岁,也为服饰研究真正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使纺织文物的种类和实物链愈加完善起来。
《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中收录了王㐨口述后整理成文字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经过,其中有一段“外行毁文物”的记录。打开一座墓中的棺椁时,椁中一共有四层棺,开到第三层时,他们发现有一幅帛画扣放在上面。王㐨现场叮嘱,谁也不要着急看,以免损坏它,完整地取回去再想办法。
“我们根据大小,做了盒子,用竹帘的棍慢慢地把它卷进去,再衬上塑料,完整地把它抬回博物馆。结果回去之后,一个搞美术的忍不住给翻过来看,有些地方就破碎了。墓里还有放在箪子里的杨梅,打开来看还是紫红色的,再拿出来看已经变成深紫色的了。当时我们没有彩色胶片,无法记录色彩,看了看表,仅十七秒,它就从紫红色又变成黑色了。我赶快把它封起来,并嘱咐不要再动,找彩色胶片来拍照。”结果,还是有人倒出来洗了。面对着剩下的一堆杨梅核,王㐨感叹,不懂业务太可怕了。
当然,这只是马王堆一号汉墓挖掘过程中的一些插曲。这里出土的两件重量分别是48克和49克的素纱襌衣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
历时4年完成的一件荒帷修复
“要耐烦!认真!”“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古为今用。”跟随沈从文工作多年的王亚蓉回忆,这是沈从文教诲他们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本着这种原则,先生在物质文化史的研
究领域贡献非凡。凭着对古代文献和杂书笔记的功底,凭着曾过目的几十万件丝绸、玉器、雕琢之骨、角、牙器等古物的鉴赏能力,沈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即开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许多预见性的推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不断地被出土文物证实。”王亚蓉在书中写到。
书中举例说,比如关于织金织物的看法。从传世和出土文物看,原来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织金物始于宋元,沈从文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织金锦》一文中提出,织金锦应始于汉唐。果然,1987年唐代法门寺地宫发掘,即出土有武则天供奉给释迦牟尼佛的织金锦袈裟,纬线全是捻金丝,捻金线的直径投影宽只有0.1毫米,且含金量很高,纺织制造技术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这些后出土的文物证实了沈从文的判断。
1991年之后,王㐨身体状况较差,王亚蓉独立主持了一些考古项目,包括北京老山汉墓、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等。在这本书中,王亚蓉讲述了发掘并修复北京老山汉墓出土的刺绣荒帷(棺罩)的经历。2000年初,北京市石景山区进行老山汉墓发掘时,工作人员发现坍塌棺板分开的一层和二层之间夹着一层丝织品。王亚荣和助手临时在墓旁搭建了一间木板房,开始丝织品的抢救性揭取保护,也开启了四年漫长的修复工作。
“纺织品出土时因墓室棺椁垮塌太久,数吨重的棺板长久紧压,将内棺荒帷顶部绣线紧紧嵌压在两层棺板内。在清理过程中,抬起外棺,荒帷顶饰刺绣再次被强力撕裂,导致内外棺顶均粘连无数荒帷残绣片。”清理和修复纺织品无比艰难,王亚蓉记录,他们观察织物发现其埋葬初期已经遭虫蛀,因墓内阴暗潮湿,一些俗称“鼠妇”(别名潮虫子、地虱婆)的尸体也因棺垮塌时,强压干枯保留在绣面上,还有棺上的铜柿蒂纹饰体、圆形铜饰件压毁造成的孔洞使绣面缺损。因此,这件荒帷清理修复过程漫长、难度很大。最终,历时4年,这件荒帷最终修复完成,并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如今,中国纺织考古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从沈从文开始,将中国纺织考古这一路走来的经历记录出来,王亚蓉期待,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服饰研究、纺织考古与纺织品保护工作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的道路,更期待有人也愿意走上这条文化传承之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考古文化繁荣。

